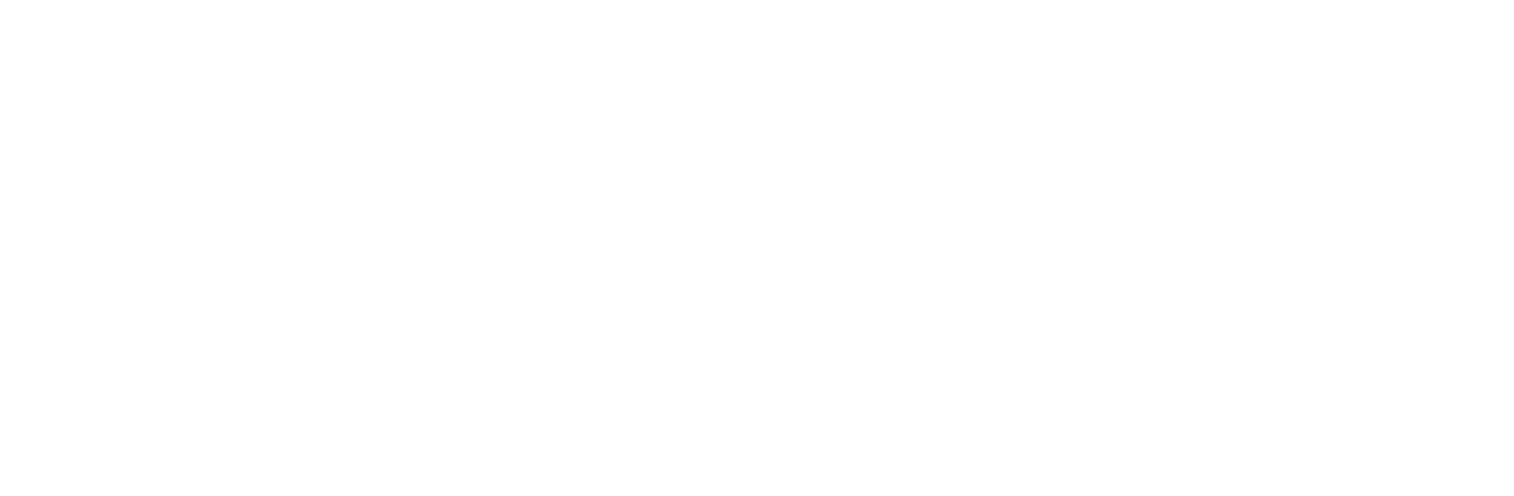作为“深圳文学文献资料”丛书(总主编张克)第一辑中的一种,首部薛忆沩作品评论集《突然显现出来的世界》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本书由何怀宏、残雪、林岗、王春林、徐刚、林培源等老中青三代评论家的25篇论文组成。利用这个机会,笔者对长年关注薛忆沩文学创作的著名评论家、中山大学文学院林岗教授进行了笔访。
作家薛忆沩
批评就是从金沙中筛出金子
冯科臣:对你来说,薛忆沩当然不是“突然显现出来的世界”。你2000年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发表《遗弃》的论文,而你最新论文是去年发表在《作家》杂志上的《薛忆沩的“李尔王”》。这两个细节表明你对薛忆沩作品的关注已有长达二十年的历史。有人相信优秀的评论家应该具备“伯乐”的目力,不仅精于鉴定有价值的作品,还善于发现有潜力的作者。充当“伯乐”是不是评论家特有的社会责任?
薛忆沩《遗弃》
林岗:你旧事重提,让我回想起了二十余年前写过《遗弃》评论一事。说起来,那篇旧文还是我迈进当代文学批评门槛的第一步。在这之前,我没有涉足过当代作家的批评。如果不是经受不起《遗弃》的“诱惑”,我真不一定会弄起批评来。这告诉我们,创作和评论实际上是一起成长的。无论创作还是批评都不会单独存在,它们的关系像生物学所讲的“共生关系”那样。有创作就会有批评,批评又离不开作品。当然作家和批评家的关注点不同,作家醉心于经验的表达,批评家专注于发掘这些经验的价值和意义,估量其表达的优劣得失。这件事不可避免地对作家和社会发生影响,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说批评是有社会责任的。批评可以毁掉有潜力的作家,批评也可以发现作家独特之处,助力作家的写作境界的提升。批评史上两方面的例子都有。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批评家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批评家。批评的社会责任有很多方面,当你看到一位有潜力的作家,当你看到一篇写得好的作品,将其推荐给更多的人,这也是社会责任之一吧。
著名评论家、中山大学文学院林岗教授
冯科臣:这部评论集收入了你两篇评论:一篇是你关于薛忆沩“文学三十年”的总结,一篇是你关于薛忆沩最新长篇小说《“李尔王”与1979》的定位。这部小说人物众多、结构错综、背景复杂……听说不少读者是在你评论的导读之下才读懂了这部“百科全书式”的作品。这让我想到“导读”也应该是评论家肩负的社会责任。你如何看待评论家在文学教育和文学普及过程中所起的作用?
林岗:“导读”是中文系必有的课程。比如“古代名著导读”“经典导读”“现当代名著导读”等。导读如同一条前人走过的路,让后来者到达阅读的目的地。既是有人走过的,就是个方便法门而已,也不排除是条弯路,毕竟自家领悟得来才是最终的领悟。要是前人走得正,像古人说的取法乎上,就能省后来者不少事儿。这便是批评家在文学教育、作品普及过程中的作用了。有时候还能起到“一锤定音”的效果。批评史上果戈理之有待于别林斯基,萨特一篇才华横溢的《加缪的〈局外人〉》更是将加缪推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。批评史上屡屡出现过见解精当、风格鲜明的批评,将开初不那么受青睐的作品变身为经典之作的事例。如果把杰作比作金子,那批评就是从金沙中筛出金子的那把筛子。金子虽然自己会发光,奈何被沙子掩住,更多的人看不到它的光芒。好的批评就是好的筛子,让金子的光芒被更多人看见。
理论变成自己的眼光,才不会有隔
冯科臣:你的评论之所以能够发挥“导读”的功效,当然是因为它做到了“深入浅出”,或者说它做到了“理论联系实际”。你从来不奢谈理论,你的理论立足于文本之“实”,又放眼于作为文本源泉的社会、人生和历史之“际”。我相信,这种评论的优雅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你古典的学养。作为古典文学的专家,你能否谈一谈现代的评论应该如何从“过去”吸取营养?
林岗:过奖了。我做的批评其实不多,批评对于我只能说是“兼职”。不过不论多少,只要笔涉,都当严肃对待。我观察到,做批评的人顾忌被人家说没有理论,于是就多多“引经据典”,反而生硬,让自己迷失在教条里。读作品就是读人生读社会。让自己有理论教养是不错的,但前提是能消化了,变成自己的眼光,才不会有隔。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。我读过的理论不算少,从古典到后现代都有涉猎。有的有道理多一点,有的有道理少一点。正因为涉猎得多,才不会变成只宗某家的“信徒”。我不敢说融会贯通,总之是天长日久,慢慢化在看事物的眼光里。哪些是哪里来的,哪些又吸取了谁人的观点,已经浑然不别彼此,也就无所谓了,连自己都不清楚了。禅宗教人不要分别人我,不要有相。借用过来,理论观念和批评者的关系正应当是这样。杜甫勉励自己“转益多师是汝师”。明明就是有渊源的,可是我们也说不出杜诗的哪一首师法的哪位前人。道理并不复杂,批评和创作一样,一切从自己的本心流出,才清澈纯明。
林岗著作封面
批评应鼓励雅正,抵抗庸俗
冯科臣:过去十多年里,一些中青年学者在你的影响之下走近了薛忆沩的作品,并且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。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,涉及到学术精神的延续性问题。让优雅的鉴赏力抵挡住平庸的勾兑和浮躁的侵蚀,这大概也是一位优秀评论家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吧。很想听听你这方面的想法。
林岗:各种不同的趣味其实一直在相互竞争着,这是一种“承认的斗争”。只要是一种美学趣味,它就天然地倾向于争取获得更大范围的承认。美学上的著名命题——美是无可争议的,其相对主义的哲学底色正在使得更年轻的一代失去辨别良莠的能力。其实美也存在可以争议的一面,而且必须争议。有的高雅,有的低俗;有的纯明,有的污浊;有的甘美,有的苦涩。连古人都意识到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,难道相对主义就可以将差异抹掉?换句话说,批评应该坚持并鼓励雅正的趣味,抵抗庸俗的趣味。正如您说的那样:“让优雅的鉴赏力抵挡住平庸的勾兑和浮躁的侵蚀。”在当代,一是由于白话文降低学习和使用语言的门槛,二是由于消费主义大行其道,文学上的粗制滥造和恶俗趣味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来得汹涌。要是任由恶俗而粗滥的趣味凭借相对主义哲学提供的方便大张旗鼓,久而久之,年轻的一代恐怕就“如入鲍鱼之肆,久而不闻其臭”了。
批评应从细处挖掘,力避笼统
冯科臣:最后问一个具体的问题。关于薛忆沩作品的研究正在升温,每年都有不少的论文答辩和发表。作为长期关注薛忆沩作品的学者,你对目前的研究中存在着哪些“不足”应该是非常清楚的。能否利用这个机会与年轻的评论家分享一下你的观察?
林岗:我甚少关注别人批评的欠缺。不过道理是很清楚的:批评的表达应当追求信息量的最大化,而力避笼统的、模棱两可的判断;把想要表达的意思推向细化,这样才能使句子的信息量饱满充足。当然如果作品平平淡淡,纵使做批评的人有从细处发掘的意识,恐怕也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。应该说,古代批评在这方面是比当代批评强的。古代批评讲究拈出“诗眼”“文眼”,并发展出评点的方式来保证这样的批评习惯得以落实。不信,只要展卷金圣叹批点水浒,对古代章回小说的精妙即能了然于心。而当代批评讲究理念先行,讲究批评者优先,作家与文本遂被置于附骥尾的地位。
如果是笼而统之评论文学现象,还不显得破绽,但遇到像薛忆沩这样叙述故事讲究细处精妙的作家,必然难得要领,批评他的小说就难免有遗珠之恨。比如他的名篇《出租车司机》,通篇讲伤感的离别,出租车司机与妻女的永别、与生活之地的离别、乘车男女的离别,怎样将这些不同的离别故事串在一起,埋下不动声色的伏线,让读者串起来品味个中含义?小说第一段最末一句:“有一滴雨正好滴落到他的脸上。”雨告别云滴落下来,用自然现象的离别暗示人间的离别;雨水暗示后文几次出现的伤感的泪水。借古人的说法,这就是“草蛇灰线之法”。还有在《首战告捷》的最后,“我”劝绝望的将军说:“我们回去吧。”而将军的回答是:“回哪里去?”这日常的问题将整部作品推进了存在的深渊。用极度细微的语言变化来呈现罕见而激烈的社会、历史和心理冲突是薛忆沩文学语言的一大特色。这些都是值得未来的评论家去深入挖掘的。
【受访者简介】林岗,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,博士生导师,著有《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》《传统与中国人》(与刘再复合著)《罪与文学》(与刘再复合著)《秦征南越论稿》《诗志四论》等。
更多阅读资讯: